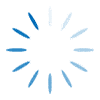余清淮在新西兰的第二年,她有了熟悉的工作搭子,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白人小姑娘,叫Georgia。两个人一起做了一个案子,案子收尾那天,Georgia随口问她要不要一起吃个午餐。
后来这种邀请逐渐增多。
余清淮想,除了王律这种领导角色,她在异国好像也有了一个朋友。
有时Georgia会约她下班后一起去超市,有时是周五下午提前收工,她会来她桌边敲敲。
她带她去了很多本地的餐厅,包括吃taco的墨西哥菜馆。
而那个时候,她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宋珂了。
唯有一次她愣神了许久。
她在她甲方顶头上司的脖子上,看到了宋珂当时送她的那个项链。
茶水间的八卦时间,同事兴致勃勃地说:
“你们知道Amanda那条项链多少钱吗?差不多三十万。”
几个人倒吸一口气。
只有余清淮沉默。
她心里五味杂陈。宋珂那时候……大概确实,很爱自己吧。
她走的时候,宋珂送的所有东西她都有没有拿走,留在了宋家。
因为她希望宋珂可以忘掉自己。
她自己呢?也好像刻意的,要去忘掉了那段往事。仇啊恨啊,已经离她很远,像上辈子发生的事情,像一场梦。
也是在新西兰的第二年,她拿国内的专科文凭去申请了Graduate Diploma的课程,半工半读的性质,读完之后,在新西兰这边,她的学历就能被算作本地的高等级文凭。
她存的钱一分都没动,全拿来教了学费。
这一年她还开始健身,新西兰全民健身,因此很便宜,她发现运动能使她头脑更清醒。
第三年,她已经能独立处理项目,而等她积累到足够的本地经验后,这边的公司给她办了Work Visa。
她的老板是个胖胖的老头,头发花白,走路慢慢的,说话也慢。
对余清淮的评价是“reliable,很可靠”,在新西兰,这是非常高的夸奖。
她还修完了学分,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竟这两年,她没有休息过哪怕一个周末。
第四年,她能自然地在早会上表达反对意见,也能跟老板很自然的谈薪资调整。
她换了住处,从最初的小房间搬到一个安静的工作室型公寓。
她又递了硕士申请。上课、做小组作业、做research、下班赶夜课、周末对着电脑写report。
多出来的碎片时间,她开始自学西语。
她的每一天都被课程和工作瓜分得一干二净。
她的同学有老头老太,也有很年轻的二十出头的男孩儿女孩儿。
她被同组的一个男生表过白,是个墨尔本男孩子。 这个表白让她猝不及防,因为她认为除了小组讨论,他们私下根本没有接触。
那男孩儿就是非常夸张且直白的夸余清淮,夸气质独特,他见她第一眼就难忘,但他知道中国女孩儿是很含蓄的,所以这么久才告白。
告白的结果自然是被拒绝,但他也无所谓,还是嘻嘻哈哈的。
Evan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但后来经常礼貌的约余清淮出去,说多个朋友总可以。
余清淮才慢慢了解Evan这个人。
他本科最后一年跟了一个做“海洋治理与法律框架”的教授,那个团队的主研究者在新西兰,所以他申请了这边的Master课程,来做两年项目。
Evan说他热爱自然。余清淮后来发现Evan的热爱,应该叫一种痴迷。
他是某个物种生存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前缀太长,余清淮没记住。只知道他世界各国到处跑,有时候要去那种地图要缩到第三层才找得到名字的小岛,而去的目的是给海龟做编号、挖沙找被偷的蛋。
余清淮其实不太能理解个人花这么大力气投入到这种飘渺的事物上去,她是个实用主义。虽不理解,但尊重。
她这些年认识了许多很奇怪、或者是超出她认知的人。
世界很大,有趣的人很多。
Evan显然就是其中翘楚。
他在同学里混得很开,这让余清淮更奇怪他会对自己感兴趣。
而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是自己的原因。
她是那门课里唯一一个亚洲面孔。她很认真,认真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在学校里独来独往,寡言少语。
漆黑的头发,没有染过,也没有卷。
在新西兰养成的健身习惯,又让她不再驼背,而是笔笔直直。因为长年吃得少,因此很清瘦。
岁月的洗礼,使得余清淮度过了漫长的寒冬,如同蓄力一般,那枝头上的花苞终于在春天到来之时,伸展了它的筋骨,迎风开出了花。
这样一朵花,尽管不招摇,但迎风招展的样子,总会被有心人注意到。
Evan觉得余清淮很神秘,几乎完美符合了他对东方女人的想象。
表白被拒后,他依然经常约余清淮出去玩,大部分时候都会被推脱,理由是“很忙”,但极少时候,她会同意。
Evan出现的节点很巧妙,在头些年,余清淮是根绷紧了的弦,是一刻不停旋转的陀螺,但在这第四年,她终于有种一切步上正轨,她的生活里除了和Georgia下馆子,允许自己有一点“娱乐”了。
更重要的是,Evan的提议经常令她无法拒绝。
他带余清淮潜水,他有潜水教练证,他教余清淮如何在水下调气、如何看潮线、如何辨别海底的暗流。
教她认珊瑚的种类,还带她夜潜,看海底荧光浮游生物。
有一个周末Evan甚至临时拖上她,飞到了科科斯方向的一串小岛上,看海龟上岸产卵。
Evan是一个钥匙,带余清淮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对于Evan来说,就是一个游乐场,而余清淮初来乍到,每一步都踩在新鲜事物里,从身到心都接受着冲刷。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