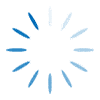这天是个难得的晴日,只是日光照在雪上,积雪融化,反倒更加寒冷。高昆毓先召见了司礼监和内阁的人。她本想去觐见母皇,可父后却说她几乎已经很少醒来,只得作罢。
她空置了龙椅,自己设了张椅子放在下方一侧,“今日召众卿进宫,不为别的,昨日的旨意已说得十分清楚。只是我年纪太轻,资历很少,于当前国事也无甚建树,还望众卿各抒己见,为我指点一二。”
她说得很谦虚,但众臣却不敢怠慢。一番寒暄之后,赵常安先领头道:“以臣愚见,最要紧事有叁件,那便是安王围京、鞑靼进犯还有各地饥荒。”
安王终究是以在地方掌握兵权坐大的,在中央,主要的势力来自吏部,吏部尚书的二儿子是安王正君,这样算来,権选的官员大多都是安王一派。但眼下敌众我寡,这吏部尚书听到赵常安直言不讳,也没有作声。
高昆毓点点头,却没提这件事,“不知这各地饥荒是怎么一回事?”
赵常安任的是户部尚书,她道:“为筹措军费,朝廷一直加赋,即便是欠收的地方,算上胥吏多征的,百姓也得交叁成的粮上去。还有,去年发洪水,官府的赈灾粮都赈了出去,短时间内没有补充足够,今年只能各地调粮,运送所需时日也甚久。不过眼下突增这么多饿殍,主要还是连日大雪,百姓饥寒交迫所致。”
白忠保看了一眼高昆毓,问:“主要的帐都算下来了,国库里还有多少钱?”
赵常安道:“新年在即,预算也得重新批。按户部一直以来记着的账簿看,国库中十分吃紧。若是此次战事还和上次一样长,百官的薪俸还得先欠一部分。”
这样说,就是一分也不剩了。高昆毓正思索哪里还能开源节流,礼部尚书道:“殿下,前些日子四殿下说,淑君此次的寿宴不再操办,镇南王府的供养减到原先的叁分之一即可。”
“哦?”她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些官员开始对宗室开支不满。但她刚刚监国,尚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旦削减供养,首当其冲的就是安王,“镇南王体恤国事十分不易,不过供养毕竟是我大齐的祖制,不可轻易变更。依我看,可以将富些的藩王的俸禄欠一欠,调一调,供给穷藩。”
当前军情毕竟十万火急,为了避免真正的造反和兵变,她也不打算削减军费。“另外,军费务必筹措到位。但必须要有限度,不能无节制地拨款。鞑靼自数月前大败、安王班师回朝后理应山穷水尽,如今只是淌浑水罢了。这次务必将他们打回去,永绝后患。”
“殿下,若打不回去呢?”吏部尚书小心翼翼地问。
白忠保看着她,冷声道:“莫大人,安王并非草莽之辈,若无百分百胜算,怎会留如此多人马在京师?”
“正是。”高昆毓摆摆手,似乎不愿多谈这最紧迫的威胁,继续道,“薪俸和供养省下来的钱先拨给各地官府买粮,不够的便借。只是风雪不止,该如何让百姓不受冻?”
赵常安道:“依照以往的法子,也会发些炭火棉衣。若是无处可去的难民,便待在施粥的木棚还有各地的官舍。若殿下实在担心,臣再呼吁百官腾出些房舍,让百姓暂住做活,再发些工钱。”
高昆毓缓缓点头,道:“也只能如此了,我等能做的,实在有限。按方才说的,内阁写好票拟,司礼监批过红,便即刻施行。”
待议事结束,高昆毓坐在椅中,看着殿门逐渐合上。她知道这些人都在等着她处置安王,不过她还真一时想不到什么好法子。议事前她私见文光秀,发了调兵的勘合,很快五军都督府、各路衙门还有兵马司的士兵便会出动,与安王的人马相持。
虽然没了正面的威胁,但谁也不能保证什么时候来个叁百刀斧手,她现在需要的是亲信。可此事急不得,姑且先等前线的军情报到宫里罢。
眼下事态严峻,到了深夜,她还在书房和白忠保、内阁的户部左侍郎蔡贤华商讨事宜。待批得差不多了,已经快到丑时。想到还要上朝,高昆毓便直接让太监们搬来床,准备睡在殿内。白忠保正收拾奏折票拟,见太女带来的叫张贞的宫男正为她擦脸,他便搁下手上东西去替她脱鞋。
高昆毓一惊,把脚抬起来,“白公公,你不必做这些宫人的活,让他来就好。”张贞应了一声。
见她有些抗拒,白忠保笑了笑,站起身,“殿下说笑了,我们这些人本就是奴,能替殿下脱靴是福分。殿下不喜欢奴才伺候,奴才便在外间值守。只是皇上那边不大好去了,皇后叫荣公公在伺候。”
见女人似乎在揣摩他这话的深意,白忠保又补充道:“有什么事,他会和奴才说的。”
高昆毓这才舒展眉头,道:“有劳公公了。”
从政事上来说,她并不信任白忠保,只是相信他不会和利益过不去。但他一直做得很到位,对她助益也大,便愿意让他顺利地参与其中。至于生活上,自然会优先张贞,毕竟他是从小服侍她到大的。
回了司礼监,白忠保坐在床上,让小宦官们替他解衣脱靴、取下巾帽,同时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苍白阴柔的脸露出些许疲态。
掌印太监,若是皇上信任,比之首辅也差不多。忠君乃是必然,然而,忠于皇上的哪个女儿却是没有定论的。他一直心中有些后悔,选择太女是否太过草率?位高权重惯了,似乎没以前那么斟酌仔细了。
若是高昆毓知道他的想法,一定会摇头。上一世,即使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当中间派,到了最后也被高正明寻了个由头处以极刑,虽说是为了打压权宦,但这种死法也极大地与高正明本身就厌恶阉人有关。
白忠保坐在木桶中,用热水和皂角搓洗自己的身体,思绪飘散:荣福是他一手提携成秉笔太监的,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心眼也没那么多,要论信得过和服侍人,还是他那样的合适。
因早年的粗活而十分粗糙的手指搓弄着疤痕——和所有上了年纪的太监一样,泄欲的后穴渐渐松垮,还有那残缺处,切了后就管不住,现在愈发需要用香囊遮掩味道。
四下无声,他站起来,带出哗啦啦的水声。
也罢,景明皇帝也活不了多久了,既来之则安之。白忠保垂眸看着水面,波澜扭曲了他的面容和夹杂银丝的头发。盘根错节的政事逐渐溶于黑暗,留下凤姿龙章的美貌。沉迷声色自然是谣传,凭他这几个月与太女的来往,宽仁谦和也只是表面。
思索着,白忠保把中衣披上。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