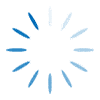最初几天的同居生活,像咖啡里逐渐融化的方糖——甜蜜缓慢渗透,却也在表面留下细小的漩涡。
瑶瑶醒来时,阳光已经铺满了半个卧室。她眯着眼看手机:上午九点十七分。这在她的作息里算“睡过头”,但在凡也这里,似乎刚好。
客厅里传来煎蛋的滋滋声。她裹着毯子走到门边,看见凡也背对着她在厨房忙活。他没穿外套,只套了件宽松的灰色卫衣,头发睡得翘起一小撮,随着他打鸡蛋的动作轻轻晃动。晨光从东窗斜射进来,给他的轮廓镀上毛茸茸的金边。
“醒了?”他没回头,像背后长了眼睛,“咖啡马上好,你要拿铁还是美式?”
“拿铁吧。”瑶瑶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
“明智的选择,”凡也转身,冲她笑了笑,“美式太苦,不适合早晨。”
这话听起来像评价,但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瑶瑶在餐桌边坐下,看着他在厨房里流畅地操作:磨豆,压粉,萃取,打奶泡——每一步都有条不紊,但不像表演,更像一种享受。
“你每天都自己做咖啡?”她问。
“差不多,”凡也端着两个杯子过来,“在漂亮国学会的奢侈享受。其实机器是二手货,但调了好几个月,现在味道不比店里差。”
他把杯子推到她面前,奶泡上真的有个粗糙的心形。瑶瑶盯着那个心形看了几秒,然后小心地喝了一口——绵密,醇厚,温度刚好。
“好喝。”
“那就好,”凡也在对面坐下,拿起自己的杯子,“对了,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瑶瑶想了想:“想继续剪片子,有几个镜头不太满意。”
“需要我帮忙吗?”
“暂时不用,我想自己先试试。”
“好,”凡也点头,没有坚持,“那我看书。下学期的工程力学据说很难,我想提前翻翻。”
他的课本摊在桌上,确实密密麻麻的公式,但旁边空白处画着些小涂鸦:一个打哈欠的小人,一只戴眼镜的猫,还有歪歪扭扭的“好困”两个字。
瑶瑶忍不住笑了:“你这是复习还是创作?”
“劳逸结合嘛,”凡也眨了眨眼,“纯看公式会睡着的。”
上午就这样开始了。瑶瑶在餐桌这头打开电脑,凡也在那头摊开课本和笔记。阳光缓慢移动,房间里只有鼠标点击声、键盘敲击声和偶尔的翻页声。
同居初期,这样的场景渐渐成了习惯。瑶瑶剪片子时,凡也就在旁边看书。起初她只是自己琢磨,直到某个下午,她被一个叙事结构的难题卡住,对着时间线皱眉叹了口气。
“卡住了?”凡也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他没抬头,笔尖还在纸上写着什么,却像能感知到她的困扰。
“嗯,总觉得这两个场景的衔接有点生硬。”
凡也这才放下笔,把她的电脑轻轻转向自己。他看了几分钟,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这里,如果加个两秒的空镜过渡呢?就像解题需要中间步骤一样,给观众一个呼吸的空间。”
瑶瑶试了试,效果出乎意料地顺畅。从那以后,她遇到专业问题时会自然地转向他。凡也的“学伴”角色仿佛无师自通——他能从她零散的描述里迅速抓住核心,给出的建议具体而开放。有次她纠结于纪录片的理论框架,第二天早餐时,凡也递来一本翻旧了的《纪录的伦理》:“第三章的论证,和你上周那篇作业的思路一脉相承,但更成熟。你可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主观视角和客观材料的。”
瑶瑶翻开书,看到他留在页边的铅笔批注,那些字迹和他课本涂鸦是同一人的手笔。她的学术自信在他的陪伴下悄然生长,但不知不觉中,完成一个段落、解决一个难题后,她会下意识地看向他,等待他点头或那句“这个切入角度很好”。依赖的种子,就在这智识的共鸣与欣赏里,静静埋入了土壤。
中午他们一起做了简单的三明治,凡也切番茄时差点切到手,瑶瑶笑他“理论派”,他也不恼,说“实践出真知”。
下午阳光最好时,瑶瑶说想出去走走。
“去哪?”凡也问,抬头从书里抬起眼,“外面很冷。”
“就校园里转转,拍点雪景,”瑶瑶已经穿上外套,“一直闷在屋里也不好吧。”
凡也放下书,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站起来:“等我一下,我穿外套。”
“你不用陪我的,我可以自己去。”
“那怎么行,”凡也已经开始穿鞋,“万一滑倒怎么办?而且两个人走路,时间过得快。”
这话听起来像关心。瑶瑶犹豫了一下,没再拒绝。
雪后的校园像被按了静音键。
雪堆积在树枝上、长椅上、路灯罩上,厚厚的一层,干净得没有脚印。空气冷冽清新,呼吸时能看见白雾。他们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咯吱作响,是唯一的声音。
瑶瑶拿出手机拍照。凡也跟在她身后,偶尔指点:“那边光线好”“这个角度可以试试逆光”。
走到钟楼广场时,瑶瑶停下来拍冰柱。屋檐下挂着一排晶莹的冰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水晶吊灯。
“真好看,”她小声说,调整焦距,“像时间凝固了。”
凡也站在她身边,也仰头看:“小时候在京城,冬天屋檐下也会有冰柱。我和我妹总想掰下来吃,我妈说脏,不让。我们就偷偷掰最小的,含在嘴里,凉得牙疼。”
“然后呢?”
“然后拉肚子,”凡也笑了,“但还是乐此不疲。小孩嘛,总觉得禁忌的东西更甜。”
瑶瑶按下快门。冰柱在镜头里美得不真实,尖锐,透明,随时会融化。
“你和你妹妹关系好吗?”她问,继续拍。
“还行吧,”凡也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她比我小八岁,基本是我看着长大的。但这两年我来漂亮国,她上初中,我们联系少了。她好像有了自己的朋友,不太爱理我了。”
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瑶瑶转头看他,凡也正低头踢雪,像个被冷落的大孩子。
“我小时候也想有个哥哥或姐姐,”她说,“一个人太孤单了。”
“但你很独立,”凡也抬头,“我觉得你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是吗?”瑶瑶不确定。
“是啊,”凡也认真地说,“你看你一个人来漂亮国,适应得很快,学习也好,还会拍片子。比我强,我刚来时连洗衣机都不会用,把室友的白衬衫染成粉色。”
瑶瑶笑了。这个画面很有凡也的风格——聪明,但在生活细节上笨拙。
他们继续走,在雪地上留下两串平行的脚印。走到人工湖边时,瑶瑶看见冰面上有孩子在滑冰,笑声尖脆,像鸟鸣。
“你会滑冰吗?”凡也问。
“不会。”
“我也不会,但我爸强迫我学过,”凡也做了个夸张的摔倒动作,“结果就是在冰上滚来滚去,像个人形保龄球。教练都放弃了,说‘这孩子重心有问题’。”
“那后来呢?”
“后来我爸说‘算了,专心学习吧’,”凡也耸耸肩,“反正他对我学业的期待,比对运动的期待高得多。”
这话说得轻松,但瑶瑶听出了弦外之音。她想起凡也的父亲——那个照片里不苟言笑的男人,用期望编织的网。
“你爸爸......”她试探地问,“对你很严格?”
凡也沉默了几秒。风把雪从树枝上吹下来,纷纷扬扬,像又下了一场小雪。
“严格这个词太温柔了。”他终于说,“他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该做到什么程度,都有标准。达不到标准换来的就是漫长的沉默。”
他弯腰团了个雪球,用力扔向湖面。雪球在冰上碎开,散成一片白雾。
“所以我逃到这里来了,”他轻声说,“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好像也能远一点。”
瑶瑶看着他。凡也的侧脸在雪光里显得有些苍白,睫毛上沾了细小的雪粉,像撒了糖霜。这一刻的他不是那个总是知道该做什么的凡也,而是另一个版本——也会困惑,也会受伤,也在寻找出口。
“但你还是很优秀啊,”她说,“成绩好,人缘好,什么都做得好。”
“因为习惯了,”凡也转头看她,笑了笑,“习惯了他那套标准,内化成自己的了。有时候我都分不清,哪些是我真正想做的,哪些是我觉得‘应该’做的。”
这话让瑶瑶心里一震。她想起自己——那些“应该”好好学习的日子,“应该”听父母话的决定,“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懂。”她轻声说。
凡也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你懂。所以我们才能成为拍档,对吧?”
拍档。这个词有了新的重量。不只是合作者,是能互相理解彼此的困境的人。
他们沿着湖边走了一圈,谁也没再说话,但沉默是舒适的,像共穿一件保暖的外套。阳光渐渐西斜,把雪地染成淡淡的金色。
回去的路上,凡也突然说:“对了,晚上我想试试做个新菜,你介意当小白鼠吗?”
“什么菜?”
“麻婆豆腐,我从一个四川学长那儿学的秘方,”凡也眼睛亮了,“他说保证正宗,辣到流泪那种。”
瑶瑶想起自己不太能吃辣,但看见他期待的眼神,还是点头:“好啊,试试。”
晚饭确实辣。
凡也一边炒菜一边打喷嚏,眼泪都出来了,还在坚持“正宗就要这么多辣椒”。成品红彤彤的一盘,豆腐嫩得用筷子一夹就碎,肉末香酥,花椒的麻和辣椒的辣在舌尖爆炸。
瑶瑶吃了一口,立刻呛到,咳得满脸通红。凡也赶紧递水,自己也辣得吸气。
“是不是......太辣了?”他问,嘴都肿了。
瑶瑶喝了半杯水才缓过来:“还好,就是......劲有点大。”
“我就说正宗嘛!”凡也得意了,但自己也被辣得直扇风。
最后这盘麻婆豆腐,他们配着两碗米饭才吃完。瑶瑶辣得出汗,额头鼻尖都是细密的汗珠。凡也也好不到哪去,嘴唇红得像涂了口红。
“下次少放点辣椒,”他总结,“或者我们提前买好牛奶。”
“还有下次?”瑶瑶瞪大眼睛。
“当然有!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凡也收拾碗筷,“而且看你这反应,多生动,比那些面无表情吃美食的视频强多了。”
瑶瑶摸着自己发烫的脸,不知道是因为辣,还是因为他的话。
饭后,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影。选了一部轻松的喜剧,不需要动脑,只需要笑。瑶瑶抱着膝盖,凡也靠在沙发另一头,中间隔着一人宽的距离。
电影放到一半,凡也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皱眉,然后按了静音。
“谁啊?”瑶瑶问。
“我爸,”凡也把手机扣在沙发上,“估计又要问学习的事。”
“你不接吗?”
“等会儿吧,”凡也盯着电视屏幕,“现在不想谈正事。”
手机又震动了几下,然后停了。凡也的肩膀放松下来,但瑶瑶注意到,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沙发扶手,一下,两下,三下,像在计算什么。
电影快结束时,瑶瑶的手机也响了。是母亲。
她犹豫了一下,接了。
“瑶瑶,吃饭了吗?”母亲的声音传来,背景音里有电视的声音,好像在放春晚彩排。
“吃了。”
“吃的什么?”
“麻婆豆腐,”瑶瑶看了凡也一眼,“朋友做的。”
“哪个朋友?”母亲的语气立刻警觉起来。
“就是......同学。”
“男生女生?”
瑶瑶咬住嘴唇。凡也似乎察觉到了她的窘迫,拿起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小。
“妈,我现在有点忙,晚点打给你好吗?”
“瑶瑶,你别骗妈妈,是不是交男朋友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留学生谈恋爱要慎重......”
“妈!”瑶瑶提高声音,“我没有!我要挂电话了!”
她挂断了,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客厅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视里传来罐头笑声,突兀而讽刺。
“抱歉,”凡也轻声说,“是不是我让你为难了?”
“不是你的问题,”瑶瑶把手机扔到一边,“是我妈......她总是这样。”
“担心你?”
“控制我。”瑶瑶纠正,“用担心的名义控制我。”
凡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刚才不应该让你接电话的。明明知道你可能不方便。”
这话让瑶瑶意外。她以为他会说“父母都是为你好”,或者“多沟通就好了”。但他没有,他承认了自己的判断失误。
“没关系,”她说,“迟早要面对的。”
电影结束了,片尾字幕滚动。他们都没动,坐在逐渐暗淡的光线里。窗外的天完全黑了,雪又开始下,细小得几乎看不见,只有路灯的光束里能看见它们旋转飘落。
“瑶瑶,”凡也突然开口,“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觉得住在这里不舒服,或者有压力,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找其他住处,或者......”
“不用,”瑶瑶打断他,声音很轻,“这里很好。真的。”
这是实话。尽管有细小的摩擦,尽管会想起母亲,尽管偶尔觉得不自在——但这里比空荡荡的宿舍好,比一个人在异国他乡面对未知的疫情好。
凡也看着她,眼神在昏暗的光线里很柔和:“那我们就慢慢来,找到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好吗?”
“好。”
他站起来:“那我去洗碗。你看会儿电视,或者休息。”
瑶瑶点点头。凡也走进厨房,水龙头打开,哗哗的水声传来。她坐在沙发上,抱着膝盖,看着窗外无声的雪。
手机屏幕又亮了。是母亲发来的长消息,她没点开。
然后凡也的手机在沙发上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是他父亲的名字,后面跟着一条未读消息的预览:“你什么时候......”
后面的字被省略号遮住了。
瑶瑶移开目光,看向厨房。凡也背对着她洗碗,肩膀微微耸起,像在承受看不见的重量。水声,碗碟碰撞声,窗外的风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这个冬夜里小小的、脆弱的安宁。
她知道这种安宁很脆弱,像冰面上的裂缝,随时可能扩大。但此刻,她选择不去看那些裂缝,只看冰面上反射的月光,和月光下他们共同的倒影。
雪还在下。温柔地,持续地,覆盖着白天所有的脚印,所有的痕迹,所有的对话和未说完的话。
而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两个人都在学习如何相处——如何在不挤压对方的前提下靠近,如何在给予关心的同时不越界,如何在糖霜般的甜蜜下,小心地绕开那些正在形成的裂缝。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